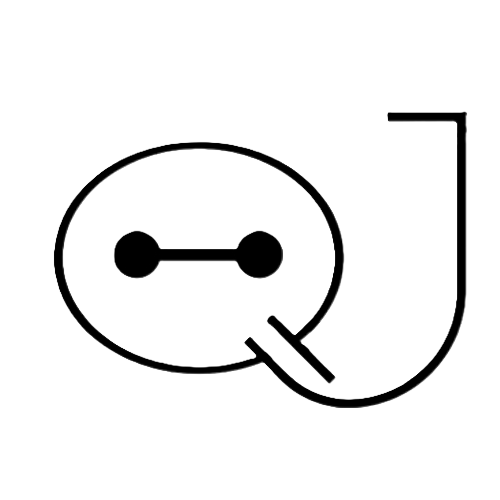父亲往事-母亲的缝纫机父亲的锯
(母亲的缝纫机)
母亲去世已多年,那年我从沈阳回到老家,看到在母亲临终前住过的屋里有一台缝纫机,台面油漆已经斑驳,虽然陈旧,但让二嫂擦的锃亮。二嫂见我凝视并轻轻抚摸着过来说:“这是母亲生前用过的缝纫机,有时用它做一些缝缝补补的小活”。“这是一台蝴蝶牌缝纫机,它陪伴了母亲的大半生”我深情地说到。
母亲是个心灵手巧的人,早年她就会十分熟练的做“纸活”,就是人们现在所说的祭祀用品:大到花圈、宅院、电器,小到各种动物、小羊、小鸟等,所有天上飞的、地下走的,无所不能,只要你能说出来没有她不会做的。
母亲小名叫“丑奴儿”,(老家奴儿就是姑娘、女子、女儿的意思)这名是姥姥起的,说是好养活。我姐姐的小名就叫“奴儿”。那时只要谁家老人去世了就说:“叫丑奴儿去”,谁家要给故去的老人做祭祀活动了也说:“叫丑奴儿去”。那时在本村母亲的手艺不是之一,是唯一。都是无偿的,甚至有时饭都不吃,那时都这样,母亲热心肠、乐于助人,随叫随到。她是一个爱面子的人,自尊心极强,人们越是鼓励,干劲越足。我们就惨了,经常不能按时吃上饭,因母亲有时一去就是一天,甚至晚上回来睡一觉,第二、三天接着去。有时母亲心疼我们这帮孩子,为了照顾好,做顿热乎饭菜,把“纸活”带家来做,说句不好听的,把我家弄的象花圈店。
那时农村出殡,不象现在都用上了小轿车,用的全是马车,妇女们每人抱一个纸做的花盆坐在马车上,男的们基本都是步行。当时有个习俗,逢有出殡的人家,人们都要抢花,说是图吉利。那些经母亲亲手做的纸花盆,被人们抢的所剩无几。但我觉得,人们除了图个吉利以外,更主要的是因母亲做的太好了,要拿回家欣赏。
使我记忆犹新的是1976年毛泽东主席去世那年,为了配合村里做好悼念活动,母亲主动承担了“纸活”,那时我家院里、屋里摆的到处是纸、花等物品,人们川流不息、摩肩接踵,把本就很小的家院挤的满满当当。当时人们胸带小白花,胳膊上箍着黑纱,个个神情凝重,还不时抽泣,诉说着主席的丰功伟绩,抒发着对他老人家的怀念之情。
话说那台母亲的缝纫机,好像是70年代买的,我印象应该是花了100—200元。当时经济条件极差,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,每年一个家庭收入也就几十元,买这台母亲梦寐以求的宝贝,得攒多长时间啊,但父亲拗不过母亲,终于到手了。计划经济的年代不是有钱就能买的,还凭票、托人。刚买回来那几天母亲喜欢的不得了,象小孩得到心爱的玩具一样,狠不得睡觉都搂着,一下不让我们碰,生怕给弄坏了。起初只用它做一些小缝、小补,或做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活儿。
母亲虽然是个文盲,大字不识一个,但爱学习、肯钻研,喜欢的事一做到底。80年代初期,社会上突然掀起了学习裁缝之风,已经快到五十知天命的年龄了,母亲正儿八经的学上了裁缝技艺。母亲是跟从晓义乡来的一个微胖的女老师学习,帮她联系三队队部做为教室,并组织学员学习,还让其免费住在我家,还供饭,答应给母亲免学费。学习裁缝的大都是大姑娘、小媳妇,象母亲这么大岁数的极少,能坚持到最后的,正真会裁缝也是凤毛麟角,母亲坚持下来了。
之后母亲自己做样板、自己裁、自己剪、自己缝,还买了不少书籍,虽然不识字,但会看图。这下缝纫机更有用武之地了,坐在缝纫机旁往往一直到深夜,甚至通宵,经常我们半夜被机器的哒哒声吵醒。有时忙的年三十日才给我们做新年的衣服,但无论多晚,大年初一肯定能让我们穿上暂新的衣服。
每年入冬农闲时,母亲的缝纫机就开始忙碌了,有皮袄、有棉服、有过年穿的衣服忙个不停当然这些活都是给别人免费做的。特别是做羊皮大衣的时候掉毛,母亲边做饭,边干活,有时饭里还能吃出羊毛来。做缝纫活是伏案的活,经常看母亲脖子上搭一条毛巾,时不时用双手揉搓双肩。有时还让父亲拔火罐,弄得后背全是水泡,但母亲从来不叫苦、不喊累,承揽的活肯定完成好。
(父亲的锯)
老宅的院里东侧有一排偏厦,墙上挂着许多木工用的锯,当然还有其他工具,但锯居多。因家人在别处建了新房早已搬出,不再居住,所有过时的家庭用品已经尘封已久,包括墙上一排排铁锯,那是父亲在世用过的工具,上面浸透着父亲的汗水,恍惚还能嗅到他的味道。
父亲的锯各式各样,得有十几把,有长的、短的,有宽的、窄的,长的有一米至二米高,短的有一尺、两尺的。父亲是个比较沉默寡言的人,脾气好,干活细,但也比较较真。据说他年轻时体质较弱,爷爷、奶奶就让其学木匠活,既能掌握一门手艺,还免得受种地之苦。
父亲的木工手艺也是村里数一数二的,经常有人找他去帮做木工活,那时跟妈给别人家做活一样都是无偿的,父亲也抹不开面子,也乐于助人,都是有求必应,一干少则几天,多则十几天。那时虽然是无偿的,但父亲在别人家干活还能吃几个小菜,喝几口小酒,干完一天活父亲带着微醺,哼着小曲回家了,很是惬意。
父亲还有几个徒弟,但印象最深的有个叫“奴三”的,闲暇时候他就会到我家,坐在炕头上与父亲请教、切磋技艺,父亲总是不厌其烦地耐心的讲解。
父亲也是有时把别人家的活带家来干,好不容易礼拜天,想休息一下,父亲拿出近两米的大锯:“来帮我锯木头”,我不好回绝,因父亲轻易不让我们干活,既然父亲提出要求我不能讲条件,那样父亲会难受的,只是隔壁小伙伴占牛(发小)还等着一起玩呢!
后来随着技术的发达、更新,出现了电动组合木工机械工具,那时大哥、大嫂已经落户北京,父亲与二哥专程去北京为大哥用电动工具打了一套家俱,二哥还因操作不小心伤到了手指。父亲担心家里情况,我是唯一在家里的“男子汉”写信时说,安慰他们,家里一切都好,还写到,母亲逢人便讲:“我比三儿吃的还胖”。父亲夸我写的好。
当初父亲想让二哥继承他木工的技术活,但据说二哥嫌太辛苦,也可能是有更高的目标追求,虽然也能干一些简单的木工活,但没有完全继承下来。
小时候,每每睏了,躺到炕上,头枕着父亲粗壮的胳膊,闻着父亲身上锯沫的味道进入梦乡。长大了从军后,探亲回家,傍晚在家乡小院中躺在摇椅上与父亲聊天,谁家老人去世了,谁家孩子结婚了一些乡村琐碎之事。
我们小时候,早晨父亲往往是那个睡醒最早的人,因要唤醒我们去上学。那时根本就没有钟表,计时的方法主要是,晴天靠天色,阴天靠鸡叫。偶尔有时因头天干活累了,第二天父亲未及时醒来叫我们上学,使我们迟到了,父亲愧疚不已,真是难为他了!
有一次,看同村条件好的家庭给孩子买了玩具手枪,羡慕的不得了,回家也緾着父母要,但苦于我家条件有限,于是父亲就自己锯了块木头,用手工,又是刨,又是锉,不到半天功夫,制作了一个木头手枪,然后再刷上黑色油漆,完全可以以假充真,我拿到小伙伴中间一显摆,他们都说好,并要换的玩一下,我当然一口回绝了。
父亲是与母亲同年去世的,母亲是夏天,父亲是冬天。走的时候没有怎么拖累儿女,这可能就是父亲的性格吧。
父亲性格极好,是个比较能忍耐的人,母亲脾气极差,每当母亲一发火父亲就不吱声,总让着母亲。有时我们在外面淘气惹祸了,父亲说,尽量别让母亲知道,免的让她生气。
父、母亲虽然走了,永远的离开了我们,那台母亲缝纫机也可能或已经被电动的所替代,也许被时代所淘汰,父亲的锯也尘封已久,但父、母的教导犹存,对我们不会讲大道理,可是他们为人处事的言行始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,我们对老人家的思念永远存在。